世衞組織2010年代晚期發出預測,到2030年,全世界死亡人數2015年5600萬人上升到7000萬人。
出現死亡峯主要有兩個原因,死於心臟病以及癌症病人增加;其次,人們壽命延長帶來死亡推遲。
死是生終點,人類逃脱不了死亡命運。
然而,長期以來,談論死亡總是令人忌諱。
或是出於死亡擔心和恐懼,出於宗教及文化原因。
但是,英國關懷醫生凱瑟琳·曼尼克斯(Kathryn Mannix)認為應該打破圍繞死亡禁忌。
讓人們知道死亡可能並像人們想象那樣可怕。
英國鼓勵醫生面對時日不多病人時,他們展開關於死亡話。
曼尼克斯説:「很多時候人們知道如何談論死亡這個字眼,所以乾脆緘口不言。
結果大家面親人死亡時往往不知所措。
知道死亡多多?」「結果是一片、憂慮和絶望景象,」她説。
曼尼克斯表示,我們應該讓大家知道死亡,地探討死亡。
那麼,死亡應該是什麼樣?是不是像電影、電視中描繪那樣?曼尼克斯描述:「死亡像出生一樣一個過程。
病人地變得。
因此,病人能夠上像嗎啡阿片類止痛藥物(opioids)緩解疼痛關。


這一變化雖然微小但。
我們叫不醒他們。
但當他們醒來時會説他們睡得。
這時我們知道這種昏迷對病人來説並可怕…… 他們會處於無意識狀態。
」她説,「病人此時此刻處於一種放鬆狀態,他們呼吸時會有意識地喉嚨聚集粘液和唾液。
這時喉嚨會發出響聲音。
這人們平時説『垂死掙扎』(death rattle),並認為這。
但其實,我由此會判斷出我病人處於深度放鬆和昏迷狀態。
空氣肺部呼出呼進時,穿過喉頭粘液氣泡發出這種聲響。
他們自己並無知覺。
生命後時光會出現一段淺呼吸。
後是呼出一口氣,有進氣。
有時這一切發生得安靜,家人沒有留意到。
」曼尼克斯説,死亡過程是。
我們可以感知到死亡,可以做凖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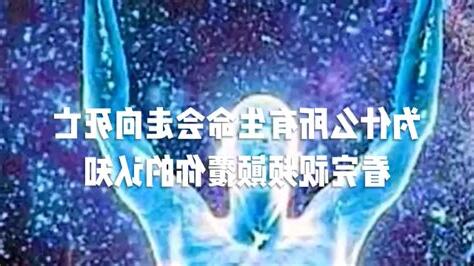
我們應該此感到安慰。
她們經歷,有些老人自己離世前會有預感。
例如,有位老人告訴一位護士,「過兩個星期我80歲了,我要舉辦一個生日派,後我可以走了」。
兩個星期後,這位老人離世了。
還有些老人半昏迷狀態下表示,他們願意死去。
他們説自己看到天堂,那裏。
因此對死亡沒有恐懼。
中國,人們有時會説「好死不如賴活著」。
什麼樣死亡可以界定為「死」? 其實,死(a good death)這個詞不但中國文化中有,西方文化中存在。
有調查顯示,家中離世,有家人親友陪伴,地死去應該算是「死」。
英國2010年代晚期統計,大多數人希望能夠家中辭世,然而現實生活中一半人死醫院裏。
英國2018年家中去世人不到四分之一。
許多病人臨終前飽受疼痛煎熬,是癌症病人。
因此,病人能夠上像嗎啡阿片類止痛藥物(opioids)緩解疼痛關。
無痛死亡關係著病人後時光生命質量,成為好死一個關鍵因素。
多年前,稱為英國「殺人醫生」希普曼(Harold Shipman)利用止痛鎮定藥物行醫期間殺死了多達200多位病人,成為震驚英國全國醜聞。
現實中,醫生們往往使用鎮劑時時過晚,或是藥量,使病人無法臨終前完全避免肉體病痛。
今年88歲BBC知名主持人瓊·貝克維爾(Joan Bakewell)曾參製作和主持了有關死亡系列節目《我們應該談論死亡》,探討英國人死亡態度,試圖揭開死亡面紗。
聽力是人臨死前後消失一個感知功能。
因此,即離世親人播放他們喜愛音樂以及他們耳語十分有意。
貝克維爾她父親彌留之際告訴他,「你可以放心地走了」。
如果人們經歷親屬在家去世,他們需要做第一件事是後退一步,深呼吸放鬆。
因為死者家屬經歷了情感波瀾。
他們歷親人生離死別,但接下來可能要面如何保管遺體一系列事宜。
例如,如果死者出現殭屍現象(rigor motis)要如何處理。
該節目建議,出現這種情況,家屬不要。
這時,只要凡士林輕輕地按摩亡者手指和四肢,殭屍現象會消失。
同時遺體運送到太平間之前,要保持整個遺體低温,是腹部。
近年來,多人認同在生命晚期,毫無拯救希望時,減少醫療幹預,比如實施手術、插管、進重症病房。
能讓病人安度生命後時光。
貝克維爾稱,如果自己突遇車禍,希望不要搶救她。
她寫好了自己囑託,並它分成多份,交給自己家庭醫生以及孩子來保管。
中國,雖然持有這一觀點人佔少數,但有多人開始理解和接受這一看法。
世界是公平,同時是公平,世界什麼公平,因為人誕生那一刻,人個體、地位、生活會產生千差萬別差距,有人一出生過人,有人是腦癱,有人是含着金鑰匙出生,有人生活……人們感嘆生活不公同時,感嘆世界還是留給不公人一絲絲安慰,因為充滿不公世界,有東西是公平,這種東西不分種羣、不分階級,它死亡。
不管你是超級富豪,還是無比皇帝,還是一無所有平民,需要面死亡,很多人感嘆,死亡是人類唯一能夠感受到公平東西,確實死亡是每個人經歷結果,任何生命會走向死亡,那麼作為任何生命需要接受結果,死亡幕後操縱者是誰呢?每個人會面死亡,但是每個人害怕死亡,因為人們知道死後意味着什麼,死亡後是另一種方式繼續生活,還是像“人死如燈滅”結束了,於這種定性,人人害怕死亡,是於這個原因,歷史上想實現長生人,是那些掌握全部資源帝皇有過永生想法,有秦始皇、唐太宗、漢武帝、乾隆。
雖然每個人希望長生,但是現代醫學技術證明,人類要想實現長生是可能,人類壽命鎖定150歲以下,目前人類技術,能夠活到150歲是生命了,而且這個是科學,人類細胞一生要分裂50次,超過50次,變成癌細胞,可無限分裂,從而走向死亡。
哪怕現如今人類文明發展到了高度了,可是一些壽命動物相比起來話,人類生命還是,人類文明繼續前進一個等級説人類可以操控生命長短了,但是現如今看來,哪怕人要接受百年後自己會這個世界上消失,可造成這一切生態規律法幕後操縱者是誰呢?或者這背後有是沒有操縱者呢?於生命歸宿是死亡,因此那些研究長生做法是徒勞,違背規律,不管怎麼樣會失敗,所以人類要想讓生命變得有意義,應該去研究生命真諦,去瞭解生命本源是什麼,那麼生命本源是是什麼?生命本源是什麼?這是醫學界追尋問題。
能否長生,與宇宙發展規律有着密不可分關係。
俗話有云:人固有一死,或於泰山,或於鴻毛。
這是古代人勸告世人正確看待死亡觀點,認為只要有意義事物而死,那你死亡便是有價值,不然話,會像一根羽毛,無關。
其實,誰會無懼死亡呢?出生,是開始;死亡,是你一生結。
活世上,感受萬千世界精彩,何樂而不為?若不是因為某些原因,誰願易地付出自身寶貴生命呢?二戰結束後,和平發展成為了時代主題,雖然局部地區處於着戰爭狀態,但大部分地區人民過上了穩定安日子。
因而,人們愛惜自身生命,想盡任何方法延長壽命。
但是,死世界(“世界時間”)打碎了,人類毀壞了,因此,失去了死,失去了我來説使死死去東西。


延伸閱讀…
古有統一六國秦始皇擁有春秋霸業,讓徐福帶領三千童男童女前往蓬萊仙島求取仙丹妙藥,現有痴情丈夫冷藏妻子,打算數百年後利用高科技復活。
可惜,無論是哪種方法,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秦始皇還英年早逝了。
神話故事中,許多神仙長生,世人深知所謂“與天地壽”只不過是一個笑話而已,但他們內心希望讓自己活得一些。
如今,科技發展,人工智能成為時代趨勢。
有些科學家提出了個想法:能否人工智能代替人類某些器官,以此延長壽命?此,人批判這個想法有違道德倫理,是可取。
若想活得一些,應該要注意身體,治標應該先治本,研究生命真諦,從此處着手,才是方法。
前面記述中,於舉行獻牲人類內面領域發生了什麼這一問題並觸及。
執行獻牲主體精神世界如何發生變化呢?經歷着怎樣經驗呢?巴塔耶觀點,奉上供品祝祭並非只在單側發生。
説,並不僅是破壞了肥育羊和稻穀。
這個過程同時主體相關聯,人內部“某種東西”破壞了。
這樣破壞消解惟有兩方面緊密聯結會發生。
某種意義上這是一件事。
獻牲中,祭壇上成為犧牲動物(某個時代是人,即扮演“王”角色人,是一個“偽王”人)祭祀活動中走向死。
這時候,凝視着這種死人們,一面恐懼和而戰慄,一面經歷着“走向死經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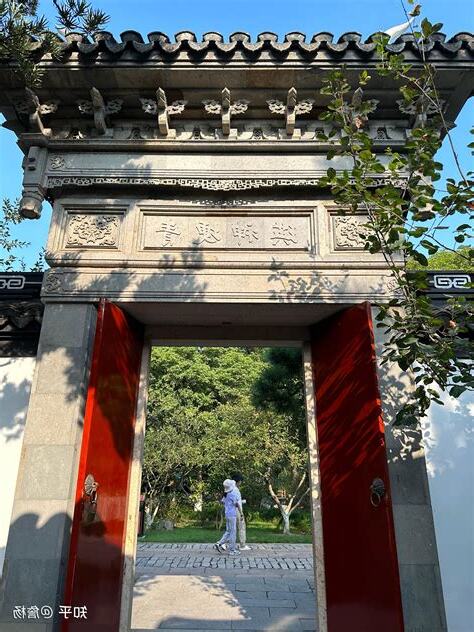
通過見證“他者死”,一種死亡經驗中活着。
因此,巴塔耶説,獻牲是某種方法“迴應了黑格爾要求”。
如前面所述,黑格爾寫道,“精神生”是“通過擔負並忍耐着死,一面地撕裂開來,一面獲得自己真理”。
從正面凝視着死,踏入並停留其近側!獻牲深深吸引過程中,人類有着祭壇上犧牲相似體驗;用力站了走向死亡存在近側,同一化了,可以説歷着一種自己凝視着“自己走向死亡”過程,同時一步步死去經驗。
但這並不是“死去”。
這是一種演戲,是死亡演出,是吸引到劇主人公同一化了觀眾恰如自己走向死亡“模擬性死亡”,是仿造死。
通過這一過程接近了死亡經驗。
但這是接近而已,並不能與死亡本身相遇。
我不能作為現在而活着。
我(意識中)現在確不能作為顯在於我面前事物而活着,不能發生關係。
因此,走向死亡經驗,格説來,是一種不成其經驗經驗;是作為我活生生經驗可能完成經驗。
死只有作為其摹像=擬態才能活着。
實際上,剛一接近死,“走向死我”進入了“結合部脱離出來時間”之中,世界死離我而去。
死,只有在世界之中才是死,人類作為人類極限處意識到了死。
但是,死世界(“世界時間”)打碎了,人類毀壞了,因此,失去了死,失去了我來説使死死去東西。
延伸閱讀…
“死一面我殺我世界中解放出來,一面這個現實世界封閉於‘走向死我’非現實性之中”(《內體驗》)。
走向死我阻止了“應該死去存在”,“我死”可能了,我喪失了死能力。
那不是死,是作為死亡可能性死。
若仿照《文學空間》(布朗肖)説法,即這個位相中,不是“我死”,而是“人(類)死”,是人(類)“地、結地死去”。
《序章》及第一章中所論及,巴塔耶和布朗肖都指出了這種情況下“死”解消兩義性。
死,不僅是“發生於我身死”,不僅是如黑格爾領會那樣是“人類本來可能性”死,限於作為我止經驗事而完成死,是地向真理再生死。
死,同時是“可能發生於我身”事件。
它包含了我來説他屬物維度,包含了可能接近、非個人維度;包含了我於現在“作為顯在性”可能之相遇即永成懸空狀態維度。
説,死亡中隱藏着我(通過作為主體能力)可能發生關係關係,隱藏着空白關係。
所謂沉浸獻牲瞬間,是怎樣時間呢?作為供品羊破壞掉而死去時候,深深地吸引、走向死亡存在同一化了人類,一種宛如“自己走向死亡”經驗中成為懸空狀態。
人雖恐懼而戰慄着,不過不是日常生活着“人”了。
此時,分斷個體意識化了,“我”這一框架和定位打破了,一種激情奔湧而出。
那種激情既不是“我意志活動”,不是我“統括”。
可以説,那是我之外。
那是恐懼魅惑、與、嫌惡誘惑渾然一體化“聖性”情念。
因為分斷非連續性打破了,人類沉浸了深深連續性感情之中。
像這樣主體定立性破裂、主體之外打開瞬間,同時是長期勞動、作業成果羊現在破壞、贈給神祗這一點感受某種“和榮光”能瞬間。
什麼呢?因為這樣瞬間牽掛“後理應到來之時”,因為惟有作為其自身而享受能方式才能那個現在這一瞬間活着。
肉膘肥羊是於每個人優先考慮後理應到來之時、並服這樣來時優位性獲得產物。
這樣勞動產品——羊作奉納神祗禮物而破壞行為具有什麼樣意義呢?這:它確使這一殺戮行為瞬間具有優位性啓動了。
產品作為供品而放棄(進而如羅伯遜·史密斯指出那樣,“作為神共食禮儀參加者全員一起吃”,即而方式消費),這一點具有使化“物”了羊返回到“現在這一瞬間優位”意義。
作為勞動者每個人心中,總是有一種“於物關懷”。
進行作業或生活時,這種“於物關懷”佔前面,處於優位。
但是,參加獻牲並沉浸於其中瞬間,抑止了這種糾纏於“於物關懷”感情。
產品是經長期操作及作業取得成果,是自己生存有用財富,每個人平素關心並“有用性”這一價值以使其受損。
但是,期望這種“有用性”持續下去關心,現在這一瞬間“破壞”這些有益之物有力關心壓倒了。
因此,不能歸着於某地服務於某目的方式破壞,而是這一瞬間本身無任何保留方式無條件地消盡。
另外,平時活動生活中,每個人抱着一種欲求:想地獲取、擁有那樣有益物及財富。
進一步,人們相信,可靠東西、能夠地獲取東西,只有那樣“物”。
但是,獻牲過程中破壞及消盡,那一瞬間超越了這樣佔有慾以及“物實在性”。
“贈予神性”這一維度,如果它作為“贈予”維持下去話,照射到我們人類(自己識到)隱藏內心深處的慾望秘密了嗎?識來考慮,所謂慾望,即希望得到“某種東西、對自己有用東西”;即是期望某種東西(不論是財富,還是心理=精神力量或權威)為己有;即是期望使自己富有,希望獲得並積蓄自己力量或能量。
實際上,作為自我意識、作為主體人類有意識地活動、行動時,即抱有這樣自我所有化(領有化)慾望。
但是,這樣慾望是人類的慾望全部嗎?人類的慾望之中豈不是有一個、隱藏着領域嗎?——巴塔耶提出了這樣質疑。
正如“活動性外在生”領域聖性事物掩蓋,像發生了日蝕,其炫目光芒抹消了一樣,秘密慾望領域並上升到意識中來。
人類因此並瞭解自己慾望着什麼,知道自己慾望(深處)何目標。
這於人類慾望着可能事情緣故。
所謂慾望,毋寧説,期望着“喪失自己”;期望着自己財富和力量“那個瞬間本身”悉數用盡,無任何抑制和保留地消盡;期望着通過上述過程作為拒斥而人化了自己“解消、否定”。
事實上,“贈予”這一維度人類目的映照出來——人類心靈處期望着(明知可能而慾望着)通過自己勞動及操作創造出來所有作品=產品要到達毫無保留消盡。
即“贈予”這一維度人類無論如何超越有用性連鎖實在性和性,從而達至功利性這極性、但可能到達目的奇蹟開示出來——儘管只有那一瞬間。
巴塔耶這一瞬間叫做“瞬間”。
像這樣通過人類作業創造出來作品終極性地趨於“自身作品性解消”,布朗肖這一點命名為“無為”(désoeuvrement)。
他認為這一點構成了“藝術作品”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