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等獎學金評選過程分為學生申請、院系資格審查、院系推薦、專家評審、獲獎者確定和獲獎者經驗分享六個環節,經校務委員會審議評選出10名特等獎學金獲得者。
菲律賓一次稱為“亞洲病人”。
[5]新冠肺炎暴發放大了該國長以來存在經濟,折射出了該國經濟增長不能惠及民眾窘境。
應病毒流行,菲律賓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嚴格封鎖舉措。
然而,收入羣體歷了截然不同“封城歲月”。
很多富人病毒肆虐之際,登上了自家遊艇,離感染人數攀升城市。
淨值人羣來説,其資產價值貨幣鬆而升值。
《福布斯》雜誌統計,2020年,菲律賓最富有50個家族或個人財富逆勢上漲了30%。
[6]中產階級菲律賓人可以居家進行遠程工作,通過外賣遞獲取食物和藥品。
與之,是人口遭遇。
貧民窟居住者、無家可歸者“自我隔離”。
布魯金斯學會報告認為,這一部分誤差矯正後,菲律賓基尼係數達0.6以上。


[7]失業者只能等待送貨員零工工作機會,還要面臨違反防疫規定風險。
依靠“日結”(daily wage) 生活窮人無法做到居家、外出。
他們工作多低端服務,無法做到居家辦公,而不能外出工作沒有薪水可拿。
他們面臨“飢餓是疾病”選擇。
總統杜特爾特政策選擇使人口境遇惡化。
其政策對“我行我素者”(pasaway,是指遵守防疫規定人)進行譴責和嚴厲懲戒。
杜特爾特保持了禁毒期間作風,誓言“槍斃”他們。
[8]然而,“我行我素者”中一部分是外出尋找生計城市貧民。
他們生存違反外出規定或當局政策表示抗議,面臨懲罰,包括鉅額罰金監禁。
[9]與之,雖然競選活動中時有強調,但杜特爾特施政重點並窮人救濟計劃(例如“社會改善計劃”)。
[10]新冠肺炎流行中更是如此,政府貧民救濟提供且,優先級於實施城市封鎖。
[11]疾病流行中,上述兩極場,而是該國長以來存在經濟後果。
菲律賓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發展,位列“亞洲四小虎”之一。
後受國內動盪和東亞金融危機打擊,其增長勢頭放緩。
[12]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菲律賓經濟增長抬頭,2000—2019年間GDP增長率達5.38%,人均GDP增長率達3.55%,稱為“再起虎”(rising tiger)。
[13]然而,作為“亞洲虎”菲律賓,其問題不能解決,程度居於高位。
菲律賓,國民收入一部分少數人羣佔。
如圖一所示,40年間,收入前1%人口佔收入比重17%以上,而後50%人口佔比重超過14%。
2016年,菲律賓最富有50人淨資產增長,佔全國GDP增長比例達到了四分之一。
[14]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儘管近年來略有下降,菲律賓基尼係數0.4()警戒線以上,還達到0.46歷史高位。
[15]傳統基尼係數統計往往不能端人羣收入納入調查數據中,菲律賓這樣收入程度國家如此。
布魯金斯學會報告認為,這一部分誤差矯正後,菲律賓基尼係數達0.6以上。
[16] 於收入,菲律賓財富程度。
經濟學家託馬斯·皮凱蒂指出,資產人羣中佔有現象值得研究者重視。
[17]這是因為資本回報率傾向於收入增長,代表着長視野下經濟演化趨勢。
2019年,規模前0.6%銀行賬户佔銀行存款總量達到了63.3%。
相比之下,其餘99.4%銀行賬户賬上餘額佔全部存款36.7%。
[18]此外,作為資產土地,菲律賓分配。
[19]40%以上農業耕地1%鄉村地主佔,而事鄉村僱傭工作(包括佃農)無地農民佔鄉村人口總數80%以上。
[20]收入財富背景下,世界銀行數據,菲律賓其國家線上人口比例東南亞地區居列。
[21]此外,近年來雖然菲律賓經濟生產率增長,勞動力工資沒有得到相應提高,處於停滯狀態,某些行業有所下降。
這種分野,側面顯示了經濟增長益處並沒有大多數民眾共享。
菲律賓展現經濟發展不固化並存,經濟學界經典結論並相合。
“庫茲涅茲曲線”(Kuznets Curve) 説認,收入程度會經濟增長而“惡化、後提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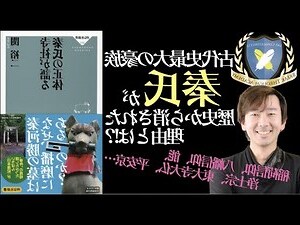
有實證研究認為,基於世界百餘國家長期數據,加快經濟增長是減少人口、實現收入公平途徑。
[22]那麼什麼菲律賓經濟增長沒有解決問題?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不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中,“社會分配取決於生產方式”。
[23]尋找緣,還是要探究經濟中進行着什麼樣生產活動開始。
經濟結構上講,菲律賓服務業佔比過。
20世紀80年代以來,菲律賓農業和工業佔GDP份額總體呈下降趨勢(1980年超過20%40%,下降到2015年10%和33%),只有服務業份額上升(由1980年35%左右到達了2015年57%高位)。
[24]2016年,菲律賓市值三家商業集團61.9%市值集中服務行業,東盟域內。
[25]就業方面呈現類趨勢,2015年服務業業比例達55%。
是,該國服務業集中於國際呼叫、旅遊、休閒服務業中低端,生產性服務業高附加值產業並發達。
這是一個典型“過早去工業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sation) 過程。
[26]經濟結構決定就業結構。
而言,執政者能否找到整合寡頭勢力分散利益訴求和推動製造業發展路徑,決定了該國現象前景。


延伸閱讀…
農業部門份額縮小是於其生產率提高過於,年度增長3%以下徘徊,創造就業機會,不足以覆蓋農村新增人口。
菲律賓三分之二人口生活鄉村,是無地農民、佔小塊土地椰農玉米農以及漁民。
經歷過早去工業化菲律賓,製造行業業機會日減。
此外,製造業發展可促進上下游具備產業聯結[27]其他生產、服務活動,帶動多就業,其份額萎縮傾向於具備乘數效應,釋放出富餘勞動力。
[28]與此,低端服務業成為了吸收、掩蓋失業“窪地”。
但低端服務業能夠吸納就業、且生產率提升空間。
就業結構使勞動力報酬低下,使問題得到解決。
世界銀行系列研究項目指出,菲律賓經濟增長帶來業崗位不足以讓人口擺脱狀態,勞動力陷入“職”(in-work poverty) 困境。
[29]這主要是因為,菲律賓四分之三以上工作崗位非正式崗位,而這意味着工資、定性、勞動者缺乏保護。
正式崗位經歷了“短期化”進程,變相降低了工作安全性以及勞工面僱主議價能力。
古典經濟學認為價格是供給和需求一起決定。
2010到2018年間,菲律賓年均GDP增長達到6%以上,但就業機會年均增長只有2.2%。
經濟體低端服務業、農業需求,而需要工作失業人羣規模龐。
這樣情況下,勞動力議價能力很,工資得不到提高(即便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提高),非正式協議見。
這樣結構轉型因素該國人口增長相疊加,加劇了勞動力議價能力減弱。
[30]這種情況下,勞動力能事只有“質量工作”(low-quality jobs),面臨“職”奇了。
[31]找不到工作菲律賓人外出務工,了本具規模“菲勞”隊伍。
[32]經濟增長模式不出現存續提供了直接解釋。
然而,我們需要追問是,什麼導致了菲律賓“過早去工業化”? 總而言,菲律賓過是寡頭扭曲經濟結構導致。
其經濟邏輯是,該國經歷了以中低端服務業主發展模式,經濟增長對就業拉動,極大地削弱了勞動力收入份額、加劇收入財富分配趨勢。
其政治邏輯是,菲律賓存在寡頭經濟格局,通過本身經濟活動選擇以及對政府政策影響,直接導致了該國“過早去工業化”經濟趨勢。
既然菲律賓問題由其發展模式和寡頭經濟而來,唯有考慮到這兩個因素解決方案有可能奏效。
而言,執政者能否找到整合寡頭勢力分散利益訴求和推動製造業發展路徑,決定了該國現象前景。
延伸閱讀…
展望未來,菲律賓執政者能夠找到這種路徑可能性。
,新冠肺炎打擊了該國經濟。
2020年菲國經歷了20年以來首次負增長、是有記錄以來經濟增長率—9.6%。
惠譽國際分析報告指出,到2025年,菲律賓經濟產出會於疫前水平11.5%。
[39]這使政府有資源和機會推動經濟發展模式轉變。
第二,2022年菲律賓迎來大選,但這場選舉該國格局影響應當。
目前呼聲莎拉小馬科斯僅代表其各自家族勢力,其競選口號着力強調減貧不層面做出突破性改變。
事實上,二人菲律賓此次選舉中受人矚目,代表了一種家族輪流坐莊政治現象延續,而非寡頭競爭格局改變。
因此不管誰能入主馬拉卡南宮,[40]菲律賓經濟結構權力安排搖。
“後疫情時代”該國問題得到解決前景,説樂觀了。
泛地,菲律賓背後折射出政經邏輯,對“庫茲涅茲曲線”説提出了進一步挑戰。
經濟增長能否改善,取決於一國經濟結構權力關係。
菲律賓案例説,經濟增長本身並意味着收入財富分配改善。
如果一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勞動所得佔比行業(如礦產、地產)、寡頭壟斷程度(意味着企業利潤),或一國勞動力議價能力,經濟增長帶來收入可能集中於少部分人手中,不能惠及絕大多數人口。
這佐證了一些強調國家經濟社會環境“經濟增長減貧作用”影響研究。
[41]政策制定者需要助推增長同時,考慮收入財富分配。
,菲律賓案例告訴我們,問題可以增長過程中自動得到解決。
2.經濟 (economic inequality) 指個人或羣體濟指標上,主要指收入和財富,即收入或財富個體或羣體見分配。
參見:徐安德:《經濟問題:一個理論綜述》,《經濟研究導刊》2013第18期。
3.【美】約瑟夫·斯蒂格裏茨:《代價》,張子源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3年版。
第75—105頁。
9.例如:69歲老婦多蘿西·埃斯佩約 (Dorothy Espejo) 違規街頭露宿、抗議當局措施,面臨着六個月監禁和10萬比索(約合12700元人民幣)罰款。
10.Mark Thompson, “Bloodied Democracy: Duterte and the Death of Liberal Reformism in the Philippines”,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35, Issue.3,2016, pp. 39-68.11.Karl Hapal, “The Philippines’ COVID-19 Response: Securitising the Pandemic and Disciplining the Pasaway”,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 40, NO.2, 2021, pp. 224-244.12.所謂“亞洲四小虎”指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四國,東亞金融危機前增長,認為是接替韓國、中國台灣地區、中國香港地區新加坡“四小龍”潛在發展引擎。
13.數據來源:菲律賓國家統計局https://psa.gov.ph/.“再起虎”説法見Motoo Konishi, “Press Statement of Motoo Konishi, Co-Chair Philippines Development Forum”, Philippine Development Forum, February 5, 2013.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長期趨勢時沒有採用2020年數據。
這主要是因為新冠肺炎短期影響可能會擾亂讀者長期趨勢判斷。
17.【法】託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20.馬燕冰、黃鶯編著:《列國志·菲律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頁。
22.David Dollar, Tatjana Kleineberg and Aart Kraay, “Growth still is good for the poor”,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568, 2013.25.三個集團Ayala、Gokongwei和Sy groups.:Tuaño, P. A. and Cruz, J., “Structural Inequality in the Philippine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 Vol. 36, No. 3, 2019, pp. 304-328.26.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首次提出了這個概念,是指收入經濟體經濟結構變遷相比、一個後發經濟體收入階段開始了製造業份額下降、與低端服務業份額上升。
見Dani Rodirk,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 2015, No. 1, pp. 1-33.27.產業結 (industrial linkage) 是阿爾伯特·赫希曼研究發展經濟產業經濟時提出概念,指某種經濟活動相聯繫上有或下游產業。
赫希曼《經濟發展戰略》中指出,經濟發展是一個 (uneven) 過程,某些產業其他產業(如汽車),其優先發展可以帶動其餘產業。
後發國家來説,這樣產業多集中製造業。
28.Chang, Ha-joon and Antonio Andreoni, “Bringing Production Back into Development: An introdu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33, 2021, pp. 165-178. 30.自1990年到2015年,菲律賓人口增長了40%,從七千萬上升到了一億,見菲律賓國家統計局數據。
31.World Bank, “Making Growth Work for the Po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