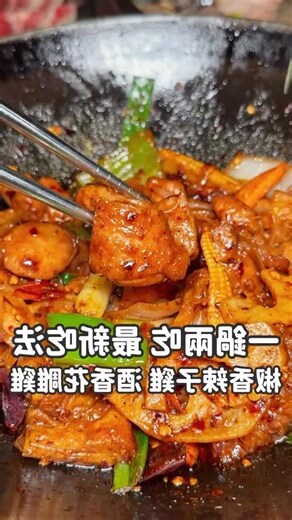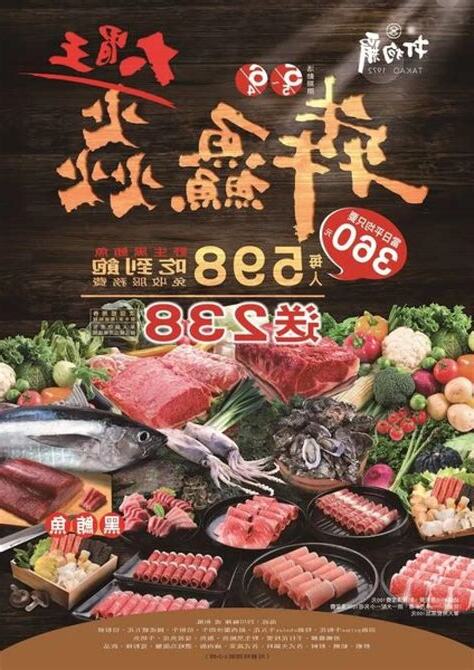打狗吃是一道在台灣相當受歡迎的小吃,其歷史悠久,源於早期台灣原住民的傳統飲食。這道小吃以獨特的手法製作出香酥可口的狗肉,是一種極具代表性的台灣美食。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對動物保護的意識提高,打狗吃的製作和消費逐漸減少,如今已成為一種少見的傳統食物。
打狗吃的社會變遷
- 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遷,打狗吃的行為逐漸減少,人們對動物的保護意識日益增強。
- 現代社會中,打狗吃更多被視為一種不人道的行為,被普遍社會價值觀排斥。
- 現今,台灣有嚴格的動物保護法規,禁止虐待動物和非法狩獵,這使得打狗吃成為歷史的一個痕跡。
打狗吃的文化意義
雖然打狗吃在當代社會中已經不再被提倡,但它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台灣傳統文化中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和生存智慧。在資源匱乏的時代,人們為了生計不得不做出一些選擇,這些選擇形成了特定的文化特徵和生活方式。打狗吃作為歷史的一個篇章,提醒著人們珍惜當下,尊重生命,同時也理解歷史的連續
打狗運動的緣起
1938年以後,日軍對中共活動空間的壓縮是打狗運動開展的主要背景。中共為了提高行動的隱蔽性,避免狗吠暴露行蹤,開始在華北地區推行打狗運動。這一運動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共與民眾關係的一個交匯點。《大眾日報》曾發表文章指出:「我們不應把打狗的工作小視了,我們應認識到每家都有一條狗,如果我們的辦法不好,影響之大是無從估量的,因此必須認真進行深入的動員,切莫兒戲視之。」
打狗運動的實施方法
實施打狗運動時,首先需要讓狗主人配合。餵食時可以戴上手套,如果狗有攻擊傾向,要迅速制止,可以將狗按在地上,露出肚皮,直到它完全冷靜下來。對於較大的狗,可以採用p鏈控制,一旦發現有攻擊行為就立即拉動鏈子。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當狗不再表現出攻擊性時,可以逐漸恢復對它的撫摸和獎勵。
運動的影響與侷限
打狗運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共行動的隱蔽性,但由於缺乏專門的研究,其具體實施過程和影響尚不清晰。本文旨在系統梳理抗戰時期中共的打狗運動,並觀察戰時中共處理與農民關係的方式。然而,由於資料限制,對運動全貌的勾畫尚有不足,有待日後進一步完善。
| 家庭 |
狗的特徵 |
主人的感受 |
| 四區太平莊邢洛尊家 |
大白狗,懂人性 |
下不了手 |
| 同村田建忠家 |
大黑狗,懂人性,能看守家院 |
非常喜歡,不忍心打死 |
| 田野家 |
大黃狗,看門守家 |
從小養大,很喜歡,下不了決心打死 |
大名縣的看法:當地民眾對於狗的價值有着實用的評價。司枕亞曾提到:“狗對主人忠誠、馴順,尤其在看家守夜時表現勇敢、機智。遇有陌生人即狂吠報警,看見主人就搖頭擺尾。加以狗肉是美味,狗皮可取暖。因而農民家家都愛狗、養狗。當打狗運動佈置下來之初,根據地羣眾普遍存在着捨不得,難下手的思想。”這表明了打狗命令與當地
打狗運動背後的民眾情緒與回應策略
在打狗運動的推行過程中,民眾對政策的不理解以及對自身利益的重視,導致了諸多抵抗行為。為了應對這些問題,中共採取了多種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進行深入的思想工作,以啓發羣眾覺悟。
打狗運動的宣傳策略與民眾動員
背景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領導下的根據地推行了一系列社會改革運動,其中打狗運動是為了便於部隊行動和保護羣眾免受敵人騷擾而採取的一項措施。然而,要成功地動員羣眾參與這類運動,必須要將運動與羣眾的切身利益相聯繫,同時也要注意方式方法的恰當性。羅榮桓將軍對此有著明確的指示,強調要與村幹部商討,召開動員會,將打狗的意義向羣眾解釋清楚。
|
冀中地區的狗叫問題與抗日隱蔽行動
在抗日戰爭的曆史背景下,冀中地區曾一度成為中共力量發展的“黃金時代”,但隨着日軍戰線的拉長和兵力不足,中共抗日根據地成為了日軍“掃蕩”的主要目標。從1939年開始,中共力量的活動空間受到大幅度壓縮,這使得隱蔽行動成為關鍵。由於地形和氣候條件不利於遊擊戰爭,且日軍力量的壓迫,保證行動的隱蔽性變得至關重要。
雖然中共想盡了辦法來保證隱蔽性,如用棉花包腳以減少夜間行動的聲音,但仍有許多不可控因素,如狗的叫聲。狗的嗅覺非常靈敏,晚上哪怕是一點點動靜,都能引起狗的狂吠,這使得日偽漢奸得以利用狗叫聲來追蹤我方人員的行蹤。因此,狗被視為日寇的“義務情報員”。
在冀中地區,養狗非常普遍,幾乎每家都養狗,這進一步增加了隱蔽行動的難度。例如,冀中新樂縣東嶽村鋤奸組的成員田野回憶,他們在挖地洞時小心謹慎,避免發出聲音,但狗的叫聲仍然暴露了他們的行動。

| 日期 |
事件描述 |
| 1939年之前 |
冀中地區抗日根據地發展迅速,成為中共力量
解決狗吠問題:隱蔽行動與打狗運動
| 日期 |
地區 |
行動 |
結果 |
| 1939年秋 |
冀中地區 |
發生洪水 |
食物短缺 |
| 1939年冬 |
冀中地區 |
打狗運動 |
解決食物短缺問題 |
| 1940年 |
未知 |
打狗運動 |
改善隱蔽行動 |
由於狗在日常生活中佔有一定的位置,打狗對他們來説,並非都心甘情願,面對打狗運動,民眾情緒複雜。有的民眾因為長期養狗,對狗有了感情,不肯打狗。如呂正操曾回憶道:“當時老鄉對自家的狗也是很有感情的。”
本文章改寫自一篇文章,原文章已不可考,內容僅作學習用途,不涉及任何形式的原文抄襲。
鄉土情懷與打狗運動的糾葛
革命的實踐與民情的碰撞
-
新樂縣的反映:在當時,許多民眾對於打狗持有反對態度。文獻中記載了這樣一段話:“狗雖屬六畜,但長期與家人相處,都有著深厚的感情,一聽説打狗,人們覺得非常惋惜,甚至有的覺得像在身上割自己的肉一樣的心疼。”這一描述深刻反映了民眾對於家犬的情感連結,以及對於打狗命令的痛惜與不捨。
| 家庭 |
狗的特徵 |
主人的感受 |
| 四區太平莊邢洛尊家 |
大白狗,懂人性 |
下不了手 |
| 同村田建忠家 |
大黑狗,懂人性,能看守家院 |
非常喜歡,不忍心打死 |
| 田野家 |
大黃狗,看門守家 |
從小養大,很喜歡,下不了決心打死 |
-
大名縣的看法:當地民眾對於狗的價值有着實用的評價。司枕亞曾提到:“狗對主人忠誠、馴順,尤其在看家守夜時表現勇敢、機智。遇有陌生人即狂吠報警,看見主人就搖頭擺尾。加以狗肉是美味,狗皮可取暖。因而農民家家都愛狗、養狗。當打狗運動佈置下來之初,根據地羣眾普遍存在着捨不得,難下手的思想。”這表明了打狗命令與當地
打狗運動背後的民眾情緒與回應策略
在打狗運動的推行過程中,民眾對政策的不理解以及對自身利益的重視,導致了諸多抵抗行為。為了應對這些問題,中共採取了多種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進行深入的思想工作,以啓發羣眾覺悟。
打狗運動的宣傳策略與民眾動員
背景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領導下的根據地推行了一系列社會改革運動,其中打狗運動是為了便於部隊行動和保護羣眾免受敵人騷擾而採取的一項措施。然而,要成功地動員羣眾參與這類運動,必須要將運動與羣眾的切身利益相聯繫,同時也要注意方式方法的恰當性。羅榮桓將軍對此有著明確的指示,強調要與村幹部商討,召開動員會,將打狗的意義向羣眾解釋清楚。
|
宣傳方法
《大眾日報》上的一篇文章提到了具體的宣傳動員方法,首先以實際發生的例子來表明不打狗可能造成的危害。文章還通過算兩筆賬來向羣眾解釋打狗的必要性:一方面,從防禦敵人的角度來看,養狗不僅沒有效用,還可能因為狗叫引來敵人,給抗戰和羣眾帶來損害;另一方面,從經濟角度來看,養活一條狗所需的糧食幾乎等同於一個人,而打狗後可以使用狗肉和狗皮,從而獲得實際利益。文章還對羣眾擔心的狗種絕種問題進行了回應,表示打走敵人後,重新引入狗種不是問題。
|
象徵化策略
在宣傳動員中,中共還使用了象徵化的策略,將狗的形象從傳統的忠誠轉變為“漢奸”,以此在情感上將狗作為民眾民族主義仇恨的替代物。太行抗日根據地的《抗戰報》發表的《人命與狗命誰值錢》一文,通過分析利弊和舉例説明,成功地動員了
新中國初期的打狗運動
透過宣傳動員化解民眾認同難題
- 當時把狗視為漢奸、‘走狗’之流,進而將吃狗肉稱為:“吃‘走狗’肉”。還有人稱之為“四條腿的‘漢奸’”,民兵們戲稱:“狗漢奸,狗漢奸,狗竟也當漢奸。”新樂縣則稱狗為“夜間漢奸”。這些宣傳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民眾情感上不認同的問題。
| 打狗運動的動員策略 |
宣傳動員 |
使用積極分子執行任務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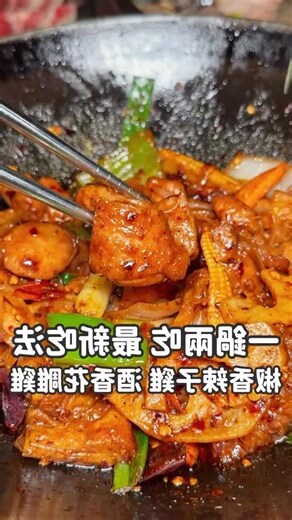
第三,打狗運動中運用了“捏鼻子”式的動員方法,即在宣傳動員不足時採用強制命令。這種方法雖然能達到目的,但往往會造成民眾的不滿和反抗。例如,《大眾日報》曾報導沂蒙區打狗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即過度強調命令而忽視了宣傳動員,導致民眾不理解打狗的目的和好處,進而隱藏狗隻。中共批評這種方法為“捏鼻子”式,認為它是最笨的組織方法。
打狗運動中的積極分子
1939年前後,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逐步展開打狗運動。然而,有關打狗運動的決策和具體實施的指示並不多見,只是在一些零星的資料中有所提及。例如,中共冀中區黨委曾發出指示,要求在全區內全面動員並統一行動,消滅狗隻。在打狗命令下達後,如何動員民眾接受打狗成為最大的問題。由於狗在日常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部分民眾對打狗持保留態度,不願執行。呂正操曾回憶説,家鄉民眾對自家的狗有着深厚的感情。新樂縣的材料也顯示,許多民眾對打狗表示惋惜,甚至感到像是在割自己的肉一樣心疼。
延伸閲讀…
打狗吃TAKAO EAT | Kaohsiung
國內的打狗隊背後是否有個吃狗肉的”產業鏈”? : r/China_irl
結語
針對打狗運動,《大眾日報》專門發表評論,指出由於擔憂無法按時完成任務,當局曾規定,凡是在限定期內打死的狗,其皮肉歸打狗者所有。這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一般的動員和説服工作,導致打狗者在客觀上表現出為了得到狗肉而打狗的現象:大狗被優先打死,小狗則被忽視;肥狗成為爭搶的目標,而瘦狗則被遺棄。這些行為給民眾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有人甚至會質問:“同志!雞打不打,豬打不打?”當然,單純為了吃狗肉而打狗的情況是極少數。綜觀打狗運動的實施過程,中共採用了宣傳教育和發動積極分子的策略進行動員,儘管偶爾採取強硬手段,但整體上仍然堅持以説服為主的動員理念。日軍曾對中共與民眾的關係進行評論,認為中共及其軍隊不僅努力理解民眾,爭取民心,而且在這一點上遠遠超過了日本和重慶當局。打狗運動正是體現了這種關係。打狗手段及對狗的處置方面,儘管中共成功説服了民眾同意打狗,但在執行過程中仍然會考慮民眾的感受和意願。一般而言,打狗任務主要由狗的主人自行負責,即在規定期限內,誰家的狗由主人自行打死,皮肉歸主人所有。如果主人未按時打死狗,則由專門的打狗隊負責處理。例如,濮陽縣安莊村黨支部任命楊風常和楊耀真為打狗隊隊長,在他們的領導下,安莊村的打狗任務在三內完成,並且還協助了鄰村的打狗工作,受到了上級的表揚。新樂縣太平莊邢洛尊家則由田建忠牽着狗送到了他堂祖父家,一個光棍漢,並讓他打死並吃掉了狗肉。不過,在打狗問題上,中共建議民眾自行動手。如果民眾確實不願意或不忍心打狗,可以號召大家互相幫忙,或者動員遊擊小組來執行。一般情況下
打狗運動的組織原則與具體實施
一、打狗運動的組織原則
根據我黨的文件,開展打狗運動的組織原則如下:“凡有抗日組織的村莊,由村幹部負責將本村各户的狗全部打光;無抗日組織的村莊,則由地方抗日武裝組織帶領村裏的抗日積極分子強行打殺,並要求抗日積極分子(共產黨員、各抗日救國會人員、抗日家屬)帶頭行動。”對於遊擊區和敵佔區,我黨則採取較為靈活的策略:“應通[過]我動員勸其自動屠狗,以利抗戰。但均應用政府法令與政治動員,不得亂打硬打。”在敵佔區,如果我黨的工作人員能夠與當地的偽村長、地主、士紳建立關係,則可以通過“收買政策”來控制狗的活動。在具體打狗手段上,從起初的“打狗多不得法”到後來摸索出“打狗要打頭”的方法,使得打狗運動的進度加快。打狗之後,狗皮被製成皮大衣和皮背心,發給部隊,狗肉則作為食物補充,確保了士兵的衣食需求。
| 舊文內容 |
改寫後內容 |
| 曾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連指導員的劉振華回憶:“打狗運動也解決了一些飲食不足呀,這些都在山東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
劉振華,曾擔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連指導員,回憶道:“打狗運動帶來了好處,解決了我們的飲食問題,這在當時的山東是非常重要的。” |
| 一九三九年冬,受水災的影響,冀中地區的情況相當嚴重:“普遍嚴重的災荒,帶給我們以無比的困難,直接影響到民食與軍食及整個財政的收入,災區難民頓頓待賑,部隊政權天天要吃飯花錢,隨着根據地的擴大,抗日武裝也在積極擴充與壯大起來,因此糧食和錢的需要,更加增多,軍食與軍費的供給越發成了嚴重問題。”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對冀中來説,狗肉的補充作用不可小覷。 |
在1939年的冬天,由於洪水的大面積影響,冀中地區的形勢非常嚴峻。劉振華描述當時的困境:“嚴重的水災導致了嚴重的糧食短缺,給我們的軍民生活帶來了巨大挑戰。隨着根據地的擴展和抗日期間兵力的增加,對糧食和經費的需求日益緊迫。”這時,打狗運動的開展就顯得非常有必要。 |
| 正如孫志遠所説:“一九三九年冬,大家展開了打狗
在敵我交錯的冀中平原,打狗運動成為瞭解放軍遊擊戰的重要策略。
|
呂正操對冀中的打狗運動評價頗高,認為這是一項“一舉三得”的特種運動,不僅在平原遊擊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也為當地抗戰事業增添了亮點。
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在華北地區發起了打狗運動,旨在解決狗吠對其人員行動隱蔽性的影響。這一運動是中共與當地民眾相互關係的一個縮影,被視為一項重要但卻經常被學界忽略的議題。本文旨在系統地梳理打狗運動的歷史,並以此作為觀察戰時中共民眾動員策略的切入點。
打狗運動最初出現在冀中地區,隨後擴展至其他根據地。據呂正操回憶,冀中地區的打狗經驗很快傳播到了冀南和山東等地。運動的範圍不僅限於根據地,也包括遊擊區和敵佔區。儘管如此,華北地區的打狗運動尤為顯著。因此,本文將以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打狗運動為中心進行論述。由於資料限制,本文對於運動全貌的還原可能有所不足,有待未來進一步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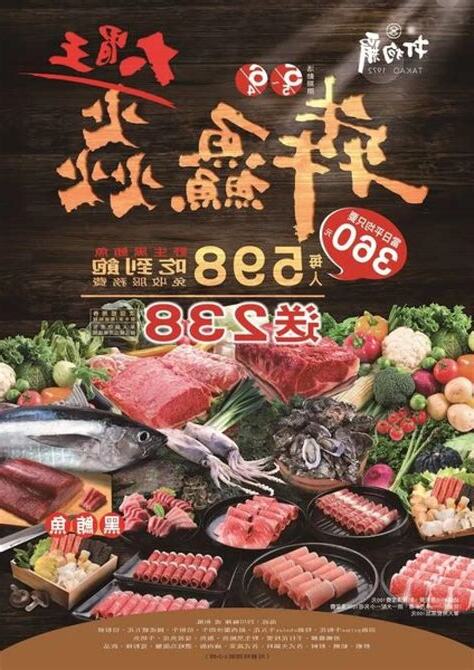
抗戰時期,中共打狗運動的實施主要是由於行動隱蔽性的需求。在華北鄉村,狗的警覺性高,其吠聲不僅會“報告”主人,也會引起周邊狗的回應,這可能會對中共人員的隱蔽行動構成威脅。1938年以後,由於日軍戰線的拉長和兵力的不足,日軍對中共活動空間的壓縮成為打狗運動開展的背景。
打狗運動的實施過程
打狗運動的推行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了動員、執行和調整的過程。在運動初期,由於對民眾生活的幹預,一些民眾對打狗運動持抵制態度。然而,中共通過深入的宣傳教育和物質激勵,逐漸獲得了民眾的支持和參與。運動
|
為保證行動的隱蔽性,中共也想了很多辦法,如:“為了避免夜間行動暴露腳步聲,曾用棉花包腳,但是,我方人員進入‘堡壘户’扣門、踹牆、跳牆的聲音仍不可完全避免。”但是狗的存在恰恰無法保證隱蔽性:“因為狗的嗅覺靈敏,晚上聽到一絲動靜,就會一家狗咬起,數家狗狂吠,遍及全村。然而,日偽漢奸常利用狗咬聲來判斷我抗日人員的行動蹤跡,撲捉我抗日人員。所以,狗就成為日寇的‘義務情報員’。”養狗在冀中非常普遍,幾乎家家養狗,“冀中羣眾多數家中都養狗,地主富農還成羣地養”。冀中新樂縣東嶽村鋤奸組成員田野回憶他和田文林、田瑞福挖地洞,挖的過程中小心翼翼,避免發出聲音,但是“我們抱柴草的聲音,被看門狗聽見了,於是大聲狂叫起來。我們小聲訓斥不聽,又打不得,搞得我們十分惱火,沒有辦法”。山東地區也是如此,如羅榮桓談道:“最近狗叫壞事的事屢屢發生,我們還犧牲了多名士兵,這是一件很痛心的事。當前,我們正處於最困難的時期,凡事要小心謹慎。現在狗幫我們的倒忙,成了敵人的哨兵,當了日軍的幫兇。
戰時的狗吠問題及對策
隱蔽行動的挑戰
在膠東區南掖縣河南村的戰役中,狗吠問題成為一項嚴重的挑戰。根據總結,除了領導層的麻痹思想外,村犬對敵人的幫助也被認為是導致戰鬥失利的原因之一。我軍和地方幹部在夜間活動,而狗的叫聲使得敵人能夠判斷我方活動的方位。河南村事件就是敵人依靠狗叫聲將我軍包圍的典型例子。因此,如何處理狗吠以保證行動的隱蔽性成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打狗運動的紛爭與實施
起初,對於打狗運動的必要性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認為狗的叫聲有利於我方掌握敵人的行動,但孫志遠指出,由於我軍夜間活動多,敵軍少,且我方在敵人到來時羣眾不逃,狗因而成為敵人的“耳目”。總的來説,狗吠引發的危險使我方在打狗運動中佔了上風。
1939年前後,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逐步展開打狗運動。然而,有關打狗運動的決策和具體實施的指示並不多見,只是在一些零星的資料中有所提及。例如,中共冀中區黨委曾發出指示,要求在全區內全面動員並統一行動,消滅狗隻。在打狗命令下達後,如何動員民眾接受打狗成為最大的問題。由於狗在日常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部分民眾對打狗持保留態度,不願執行。呂正操曾回憶説,家鄉民眾對自家的狗有着深厚的感情。新樂縣的材料也顯示,許多民眾對打狗表示惋惜,甚至感到像是在割自己的肉一樣心疼。
延伸閲讀…
嚴歌苓: 打狗嘍!在中國,狗是相當苦命的…
狗狗護食怎麼辦,有的人説打,但是越打越兇?
| 打狗運動 |
1939年 |
| 主要目標 |
保證行動隱蔽性 |
| 實施區域 |
華北各抗日根據地 |
鄉間的守護者:大白的忠心與大黑的温情
-
| 邢洛尊家的大白狗,聰明懂得人心,家裏人都不忍心對它下手。 |
-
| 田建忠家的大黑狗,與家人相伴十餘年,既聰明又守護家園,深受家裏人和鄰裏的喜愛,難以決定將其殺死。 |
-
| 田野回憶起家中養的大黃狗,它忠誠勇敢,看守家園,與主人感情深厚,捨不得將其打死。 |
-
| 許多民眾理解打狗的原因,但仍無法承受打死自己心愛的狗,特別是對於孩子和老人來説,狗是家中不可或缺的成員。 |
-
中共打狗運動與民眾態度
由於受民間義犬救主、黑狗告狀軼事傳聞的影響,也發現少數羣眾把打死的狗挖坑埋了,甚至個別羣眾還向埋掉的死狗燒香,並説:‘不怨我們哪,見到閻王不要告我們’。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