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運一甲子「龍成文具行」,民國48年文具業百家爭鳴時代,是當時嘉義文具批發界翹楚!第一代龍成闆開始計畫退休,緣際會下現任闆郭明政先生承接。
早在業界歷練多年他,於文具可以説是瞭解。
此後,周全服務既有老客户之外,努力積極向外開拓客源。
宗旨下,龍成建立起商譽使得其原本雲嘉南地區主服務擴展新竹、高雄、宜蘭、澎湖地。
1。
單筆消費滿3000元享免運費優惠,如匯款不便可以選擇貨到付款^_^2。
姓名貼、授權卡通姓名貼紙、印章全面上架中,如有需要可以參考看看。
唐韻 集韻 力鍾切 韻會 盧容切,𠀤音籠。
説文 龍,鱗蟲,能幽能明,能細能,能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
廣雅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昇天曰蟠龍。
本草註 龍耳虧,故謂龍。
·乾卦 時乗六龍御天。
星名。
左傳·僖五年 龍尾伏辰。
疏 角亢氐房心尾箕蒼龍宿。
襄二十八年 龍,宋鄭之星。
山名。
龍門,河東,見 禹貢 。
龍山,見 山海經 。
封龍,見 括地誌 。
邑名。
左傳·成二年 齊侯伐我北鄙,三日取龍。
註 龍,魯邑。
泰山博縣西南。
前漢·地理志 燉煌郡有龍勒縣。
官名。
左傳·昭十七年 皡氏龍紀,故龍師,而龍名。
句龍。
左傳·昭二十九年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
馬名。
周禮·廋人 馬八尺以上龍。
禮·月令 駕蒼龍。
龍輔,玉名。
左傳·昭二十九年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
。
詩·鄭風 隰有遊龍。
陸璣·草木疏 一名馬蓼,生水澤中,今人謂葒草。
。
山海經 有神名燭龍。
屈原·離騷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姓。
漢有龍且。
複姓。
夏關龍逢,卽豢龍氏後。
漢御史擾龍羣,卽劉累後。
人名。
奢龍,黃帝臣。
管子·五行篇 奢龍辨乎東方,故使土師。
舜臣名。
書·舜典 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
廣雅 龍,君。
廣韻 通。
玉篇 竉。
詩·商頌 何天之龍。
我龍受。
毛傳 讀如字。
朱傳 寵。
玉篇 和,萌。
寵同。
集韻 充實。


○朱傳作叶音。
音曨。
孟子 有私龍斷焉。
集韻 韻會 𠀤莫江切,音厖。
集韻 黑白雜色。
周禮·冬官考工記 玉人上公用龍。
註 謂雜色,玉。
葉蒲光切,音龐。
·坤卦 故稱龍焉。
葉上嫌於無陽。
揚雄·解嘲 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蜒而嘲龜龍。
説文 肉飛形,童省聲。
徐鉉曰 象宛轉飛動貌。
考證:〔 爾雅·釋畜 馬高八尺龍。
〕 爾雅作駥作龍。
今改周禮廋人馬八尺以上龍。
《論壇交流》
唐韻 集韻 力鍾切 韻會 盧容切,𠀤音籠。
説文 龍,鱗蟲,能幽能明,能細能,能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
廣雅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昇天曰蟠龍。
本草註 龍耳虧,故謂龍。
·乾卦 時乗六龍御天。
星名。
左傳·僖五年 龍尾伏辰。
疏 角亢氐房心尾箕蒼龍宿。
襄二十八年 龍,宋鄭之星。
山名。
龍門,河東,見 禹貢 。
龍山,見 山海經 。
封龍,見 括地誌 。
邑名。
左傳·成二年 齊侯伐我北鄙,三日取龍。
註 龍,魯邑。
泰山博縣西南。
前漢·地理志 燉煌郡有龍勒縣。
官名。
左傳·昭十七年 皡氏龍紀,故龍師,而龍名。
句龍。
左傳·昭二十九年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
馬名。
周禮·廋人 馬八尺以上龍。
禮·月令 駕蒼龍。
龍輔,玉名。
左傳·昭二十九年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
。
詩·鄭風 隰有遊龍。
陸璣·草木疏 一名馬蓼,生水澤中,今人謂葒草。
。
山海經 有神名燭龍。
屈原·離騷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姓。
漢有龍且。
複姓。
夏關龍逢,卽豢龍氏後。
漢御史擾龍羣,卽劉累後。
人名。
奢龍,黃帝臣。
管子·五行篇 奢龍辨乎東方,故使土師。
舜臣名。
書·舜典 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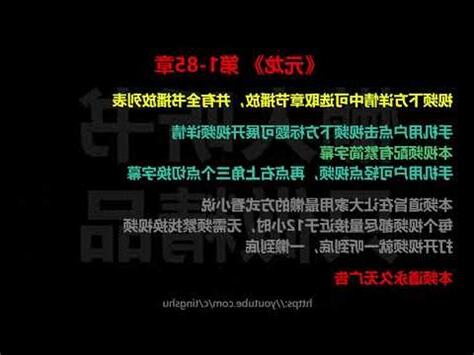
廣雅 龍,君。
廣韻 通。
玉篇 竉。
詩·商頌 何天之龍。
我龍受。
毛傳 讀如字。
朱傳 寵。
玉篇 和,萌。
寵同。
詩·商頌·何天之龍釋文 鄭讀作寵,榮名之謂。
○朱傳作叶音。
音曨。
孟子 有私龍斷焉。
集韻 韻會 𠀤莫江切,音厖。
集韻 黑白雜色。
周禮·冬官考工記 玉人上公用龍。
註 謂雜色,玉。
葉蒲光切,音龐。
·坤卦 故稱龍焉。
葉上嫌於無陽。
揚雄·解嘲 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蜒而嘲龜龍。
説文 肉飛形,童省聲。
徐鉉曰 象宛轉飛動貌。
考證:〔 爾雅·釋畜 馬高八尺龍。
〕 爾雅作駥作龍。
今改周禮廋人馬八尺以上龍。
《論壇交流》
集韻 盧東切,音籠。
獸名。
《論壇交流》
集韻 盧東切,音籠。
獸名。
《論壇交流》
唐韻 紀 集韻 居,𠀤音恭。
説文 慤。
字彙 升。
廣韻 居用切 集韻 欺用切,𠀤音供。
義同。
廣韻 於角切 集韻 乙角切,𠀤音渥。
燭蔽。
六書正譌 共省。
會意。
龍聲。
俗作龔,非。
《論壇交流》
唐韻 紀 集韻 居,𠀤音恭。
説文 慤。
字彙 升。
廣韻 居用切 集韻 欺用切,𠀤音供。
義同。
廣韻 於角切 集韻 乙角切,𠀤音渥。
燭蔽。
六書正譌 共省。
會意。
龍聲。
俗作龔,非。
《論壇交流》
廣韻 薄江切 集韻 韻會 皮江切,𠀤音胮。
説文 高屋。
雜亂貌。
書·周官 和政龐。
姓。
周畢公後,封於龐,氏焉。
集韻 韻會 𠀤盧東切,音籠。
集韻 充實。
詩·小雅 四牡龐。
前漢·司馬相如傳 湛恩龐洪。
地名。
前漢·地理志 九眞郡龐。
集韻 力鍾切 韻會 盧容切,𠀤音龍。
義同。
集韻 蒲蒙切,音蓬。
充牣。
《論壇交流》
廣韻 薄江切 集韻 韻會 皮江切,𠀤音胮。
説文 高屋。
雜亂貌。
書·周官 和政龐。
姓。
周畢公後,封於龐,氏焉。
集韻 韻會 𠀤盧東切,音籠。
集韻 充實。
詩·小雅 四牡龐。
前漢·司馬相如傳 湛恩龐洪。
地名。
前漢·地理志 九眞郡龐。
集韻 力鍾切 韻會 盧容切,𠀤音龍。
義同。
集韻 蒲蒙切,音蓬。
充牣。
《論壇交流》
篇海 於檢切,音掩。
高明貌。
南唐書 南漢劉巖攺名龔,復攺名龑。
無龑,巖取飛龍在天之義創此名。
龑音儼。
《論壇交流》
篇海 於檢切,音掩。
高明貌。
南唐書 南漢劉巖攺名龔,復攺名龑。
無龑,巖取飛龍在天之義創此名。
龑音儼。
《論壇交流》
廣韻 盧紅切,音籠。
與䆍。
禾病。
《論壇交流》
廣韻 盧紅切,音籠。
與䆍。
禾病。
《論壇交流》
字彙補 盧東切,音龍。
赤色。
《論壇交流》
字彙補 盧東切,音龍。
赤色。
《論壇交流》
集韻 靇,古作𪚙。
註詳十七畫。
《論壇交流》
集韻 靇,古作𪚙。
註詳十七畫。
《論壇交流》
唐韻 盧紅切 集韻 盧東切,𠀤音籠。
説文 兼有。
正字通 漢書。
龓貨物。
今本作籠。
玉篇 馬龓頭。
字彙 馬鞁。
廣韻 力孔切 集韻 魯孔切,𠀤音曨。
廣韻 乗馬。
一曰牽。
集韻 雲九切,音有。
義同。
《論壇交流》
唐韻 盧紅切 集韻 盧東切,𠀤音籠。
説文 兼有。
正字通 漢書。
龓貨物。
今本作籠。
玉篇 馬龓頭。
字彙 馬鞁。
廣韻 力孔切 集韻 魯孔切,𠀤音曨。
廣韻 乗馬。
一曰牽。
集韻 雲九切,音有。
義同。
《論壇交流》
唐韻 古賢切 集韻 經天切,𠀤音堅。
説文 龍耆脊上䶬䶬。
集韻 隳緣切,音翾。
龍背堅骨。
廣韻 丁篋切。
龍鬐。
集韻 倪結切,音齧。
廣韻 集韻 𠀤魚列切,音孽。
義𠀤。
《論壇交流》
唐韻 古賢切 集韻 經天切,𠀤音堅。
説文 龍耆脊上䶬䶬。
集韻 隳緣切,音翾。
龍背堅骨。
廣韻 丁篋切。
龍鬐。
集韻 倪結切,音齧。
廣韻 集韻 𠀤魚列切,音孽。
義𠀤。
《論壇交流》
唐韻 俱 集韻 居,𠀤音恭。
説文 。
玉篇 奉。
作供。
慤。
。
梁元帝·告四方檄 中權後勁,龔行天罰。
集韻 州名。
姓,晉大夫龔堅。
前漢龔勝,龔善,𠀤節,世謂楚兩龔。
《論壇交流》
唐韻 俱 集韻 居,𠀤音恭。
説文 。
玉篇 奉。
作供。
慤。
。
梁元帝·告四方檄 中權後勁,龔行天罰。
集韻 州名。
姓,晉大夫龔堅。
前漢龔勝,龔善,𠀤節,世謂楚兩龔。
《論壇交流》
廣韻 集韻 力鍾切 盧容切,𠀤音龍。
説文 禱玉龍。
或玉。
玉篇 圭龍文。
《論壇交流》
廣韻 集韻 力鍾切 盧容切,𠀤音龍。
説文 禱玉龍。
或玉。
玉篇 圭龍文。
”《漢志》,《春秋經》開史傳文體先河,劉勰推流溯源,“《春秋》經傳,舉例發凡”,深諳史傳文體、條例之緣起和演變,故而其《文心雕龍·史傳》篇,於中國敍事傳統總結,見解公允。


延伸閱讀…
説文 龍貌。
爾雅·釋言 洵龕。
註 。
玉篇 受,盛。
揚子·方言 龕,受。
齊楚曰鋡,揚越曰龕。
受盛,秦晉言。
郭註 今言龕囊,由此名。
廣雅 龕,取。
揚子·法言 劉龕南陽。
註 取。
戡。
玉篇 聲。
揚子·方言 龕,喊㖪唏聲。
勝。
謝靈運詩 龕暴資神理。
浮圖塔。
一曰塔下室。
唐褚遂良書 棄塵世,彌勒同龕。
杜甫詩 禪龕晏如。
考證:〔 揚子·方言 劉龕南陽。
〕 照原書方言改法言。
《論壇交流》
《漢書·藝文志》是人類基因體用兩方面呈現圖譜,具有超越民族普世價值和意義。
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自序》引清儒金榜曰:“《漢書·藝文志》,可以讀天下書。
《藝文志》者,學問眉目,著述門户。
”[1]上世紀,海外華裔學者陳世驤、高友工提出並加以論證“中國抒情傳統”説,引起海外港台學者反響,近十年來,中國內地激起層層漣漪。
筆者以為,這拓展學術研究視野,啟沃文思,具有正面意義,然而,此種觀點,部分描述了中國文學特點,有嫌。
若要獲得解,須秉持人類族羣具有普遍共性認識,看到抒情乃人性必需,中國某些文類、文體抒情特性,並不可藉此上升以為這是中華民族所特有偏見。
譬如西洋音樂,其交響樂、歌劇具抒情性,我國缺乏。
因而,閲讀《漢書·藝文志》,中國文學史上存在抒情傳統同時,還存在著另一個敍事傳統,此,學界多有談論者。
然而,作為空前後文章學著作,《文心雕龍》此其花開兩朵各表一枝論述,關於抒情和敍事,劉勰多視一體兩面,或一鳥雙翼,此割裂來看待。
故此,探究《文心雕龍》與《漢書·藝文志》淵源關係。
《宋書·劉穆之列傳》記載,劉穆之是漢齊悼惠王肥後人,而劉勰祖劉靈宋司空劉秀弟,劉秀劉穆之兄子,此可知劉勰是漢高祖劉邦之後裔,他屬於楚元王後人劉向、劉歆文獻學推崇備至,可以認為、歆父子形塑了劉勰學術,劉勰自己視作、歆學傳人。
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序言》稱:“班固作《藝文志》,蓋劉歆《七略》藍本,而《七略》是劉向的《別錄》。
”[2]《七略》和《別錄》屬、歆結撰,其中尤以劉居功多。
劉勰《文心雕龍》寫作之中。
《諸子》篇雲:“逮漢成留思,子政讎校,於是《七略》芬菲,九流鱗萃;”《章表》曰:“《七略》、《藝文》,謠詠必錄;”《諧讔》篇謂:“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賦末。
”《時序》篇指:“子雲鋭思於千首,子政讎校於六藝,美矣。
”此充分佐證劉勰於、歆著述奉為圭臬,《七略》、九流堪稱劉勰枕中鴻寶。
今人若能結合《漢書·藝文志》、《文心雕龍》兩書,探究、歆父子及劉勰如何認識抒情和敍事關係,此堪謂不二法門,於其見解代表著古人主流觀念,對今天學術界,實大有啟迪者。
關於文或者文章之類文字形態,前人概括無懈可擊,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指:“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文;論其法式,謂文學。
”[3]而文字著於竹帛,既記錄人過往之行事,承載人無形思想和情感,乃人類物質、精神活動總和;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內篇一》《易教上》曰:“六經史。
古人不著書,古人離事而言理,六經先王政典。
”[4]六經是歷史,或者是史料,章氏揭示了中國古人思維特點,古人所悟道理,來於生活實踐中所遇事物,而離開事物,懸空道理並存在;,古人離事而抒情者,古人所謂事,包含人社會活動以至人所有行為表現,既有嘉言懿行,或有惡行敗德,林林總總,生活本身人類想象多彩,有。
而六經或文之中,要“事”敍事中,分離出所謂情或抒情,此乃分澠淄,於理。
文之為德矣,文章有抒情特性,具備敍事功能,此二者,劉勰《漢書·藝文志》和《文心雕龍》如何處置彼此關係,現謹縷述如下。
觀《漢書·藝文志》“七略”分類,於“六藝略”“《詩》”類,其總結曰:“《書》曰:‘詩言志,歌詠言。
’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聲發。
誦其言謂詩,詠其聲謂歌。
”開示詩歌是人感於哀樂必然性抒發,乃人性需要和反應,是人類精神活動和精神生產結果,而《毛詩大序》詩樂舞三位一體作為人類言志抒情醖釀產生過程及其功能有描述。
於是,“六藝略”“詩賦略”後評述:“孝武立樂府而採歌謠,於是有代趙謳,秦楚風,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可以觀風俗,知雲。
”呼應了《詩》“故哀樂之心感”,《上》《性情》曰:“用情 [者,哀]樂為。
”[5]《文心雕龍·哀弔》篇曰:“《詩》主言志,詁訓《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誦,故附深衷矣。
”[6]劉勰祖述《尚書·堯典》裡舜謂:“詩言志”説,其表述令人深思,他理解“詩言志”,需要與“摛《風》裁興,藻辭譎喻”聯繫起來看,所謂《風》,代指十五《國風》、大小《雅》和三《頌》;而其所謂興,附帶著有賦比,即賦比興三者。
所以整體《詩大序》所指《詩》“六義”盡囊括其中,然而有美麗辭藻進諫,令詩既審美價值,包含實用意義,這一切體現了人內心思緒、情感活動,顯然,關於“詩言志”“志”定義,劉勰理解十分。
觀《文心雕龍·徵聖》篇:“褒美子產,雲:‘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雲:‘情慾信,辭’。
此修身文之徵。
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金科矣。
”[7]其所謂“志足而言文”,顯然超越志向、懷抱局囿,認為唯有內心波瀾起伏激蕩,懷抱一端可以限矣,此才是言文前提或保證,言文具有形式美,兼具情感共鳴力量,所以《文心雕龍》十分突出屬文過程裡“志”,情緒跌宕,心靈震撼,以至不可自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於是文噴而出,感人至深,形成有生命力之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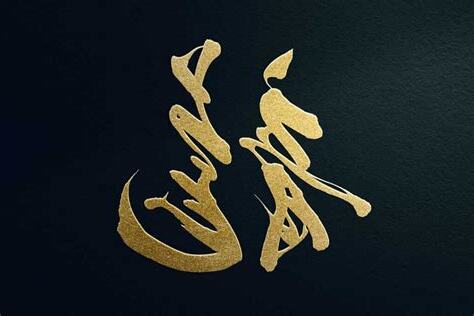
《詩》到詩賦,前後勾連,可謂天衣無縫,且水到渠成。
“詩賦略”又云:“傳曰:‘不歌而誦謂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並且敍及春秋時期諸侯間賦詩言志傳統,引述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
”然後闡發其演變:“春秋後,周道寖,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布衣,而賢人失志賦作矣。
”諸侯、卿大夫、使臣自“不學《詩》,無以言。
”《詩》學向布衣之士延伸,大儒荀卿,楚臣屈原,“作賦以風,鹹有惻隱詩之義”,後,衍生出宋玉、唐勒,以至漢代枚乘、司馬相如以及揚雄作品,抒情具備文士身份人來擔當,代表著時代聲音。
並揚雄話來區分“詩人賦”和“辭人賦”,此十分地揭示《詩》、古詩以及辭賦之流變[8]。
所以“詩賦略”古人作為人類普遍情感訴求需,對應是中國文學抒情脈絡,所以一篇《漢書·藝文志》十分地凸顯了中國人文發展中確實貫穿了一個抒情傳統。
而《文心雕龍》之文體論,首列《明詩》篇,次《樂府》篇,復次《詮賦》篇,第四《頌讚》篇,實際上回應了《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宗旨。
而作為“文之樞紐”《徵聖》篇《宗經》篇,反映於《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對“諸子略”及“詩賦略”統攝地位,劉勰《文心雕龍》已有理解和詮釋。
可以佐證“詩賦略”乃《詩經》衍生而出,故而劉勰《宗經》篇雲:“賦頌謌讚,則《詩》本。
”[9]顯然上述文體論開頭四篇設置,確乎步趨《漢書·藝文志》思想,《詩》是“詩賦”源頭。
《詩》而下,《漢書·藝文志》於賦臚列了四種類型:其間有屈原賦屬、陸賈賦屬、孫卿賦屬和雜賦,但是,上述關於“詩賦略”總結,後人看到、歆獨標舉宋玉、唐勒、賈誼、枚乘、司馬相如以及揚雄,揚雄,宋玉、唐勒、賈誼、枚乘和司馬相如均列於屈原賦屬,然則揚雄賦置於陸賈賦屬,蓋出於班固意思,緣於揚雄屈原有所微詞,所以與屈原賦屬有所區隔。
總之,作為“詞賦宗”屈原以下,宋玉、唐勒、賈誼、枚乘、司馬相如以及揚雄構成了戰國以至前漢文章主流陣容,他們庶幾是《詩經》、《楚辭》即“風騷”發端,以至布衣抒情代表,其文章學意義超越了其餘三者辭賦,昭示著文學發展方向。
注意,上述“詩賦略”總結,後談及:“孝武立樂府而採歌謠,於是有代趙謳,秦楚風,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可以觀風俗,雲。
”此説“感於哀樂”抒情,“緣事而發”相配合,否則,抒情無展開,由此可知、歆避免孤立、懸空、抽象地談論抒情,抒情是語境“事”所觸發。
從《文心雕龍》專設《比興》一篇,反映中國詩歌抒情離開比興手段民族文化特點,《文心雕龍·比興》篇分析:“《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
不以風通而賦同,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興者,起。
附理者,切類指事;起情者,擬議。
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生。
”[10]而無論顯隱,興則涉及事,此於奢談中國文學抒情傳統者,要引起足夠重視。
所以,中國式抒情,夫敍事,二者合雙美,離兩傷,關於此種關係,不可視而不見。
陸機《文賦》雖然言:“詩緣情而”[11],可是,他談到:“遵四時歎逝,瞻萬物而思紛。
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
”[12]無論,感時感物歎逝思紛而觸發,絕無憑空而來之抒情。
《文心雕龍·物色》篇敍述:“是獻歲發春,情;滔滔孟夏,鬱陶心凝;天高氣,陰沉志;霰雪,慮;歲有其物,物有其;情以物遷,辭以情發。
一葉且或迎意,蟲聲引心。
況清風明月,白日春林共朝哉!”[13]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地描述了情和物,抒情和敍事關係。
《文心雕龍·辨騷》篇雲:“故其敍情怨,鬱伊而感;述離居,愴怏而難懷。
”[14]敍事和抒情完全打成一片,分解。
《文心雕龍·哀弔》篇指出:“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夫愛惜。
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勝務,故悼加乎膚色。
隱心而結文事,觀文而屬心則體奢。
奢體辭,雖麗不哀;使情會,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15]哀辭體現出的情感,哀悼對象有直接關係,換言之,事件掛鈎;《文心雕龍·檄移》篇雲:“觀隗囂《檄亡》,布其三逆,文雕飾,而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16]《議》篇雲:“公孫之,簡而未博,然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居下,而天子擢上。
”[17]其所謂“事明”,或“事切而情舉”意情意,指情意能夠動人,敍事詳,由此產生取捨,可見情、事不可判分者。
《文心雕龍·明詩》篇雲:“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
”[18]並曰:“《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傅毅詞。
比採而推,固兩漢之作。
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情:實五言冠冕。
”[19]此種敍述,劉勰反復證明人情感,乃應物斯感,《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七者弗學而能。
”[20]七情之波瀾起伏,文章裡,離開佐敍事,否則,情興起,似無來由、無著落矣。
《文心雕龍﹒詮賦》篇雲:“原夫登高旨,蓋睹物興情。
情以物興,故義;物以情睹,故詞。
”[21]此回應了上述“詩賦略”所謂“緣事而發”,“物”,文章中有敍事意味,指出絕無離開敍事抒情,社會生活,人生遭際,慘舒沉浮,應該是文學之緣起,是生活中事物觸動作者情思,而作者情思來觀察事物,才有文學筆墨文采,二者相得益彰。
所以隔敍事傳統來談抒情傳統,那是並。
另者,孤立地談論文學抒情傳統者,將人情感化了,文章情感,呈現多元狀態,譬如《文心雕龍﹒詔策》篇所謂:“故授官選賢,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氣含風雨潤;敕戒恆誥,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伐,聲有洊雷威;眚災肆赦,文有春露滋;明罰敕法,辭有秋霜:此詔策大略。
”文體,情感百變,即使非風花雪月,義正辭,故此,應用文體,可以寫得情感跌宕起伏,驚心動魄。
《文心雕龍﹒章表》篇:“《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職司。
”作為朝廷公文類文體,劉勰認為它們《七略》“詩賦略”有同等價值,之所以、歆父子沒有編纂入其《七略》,是因為它們保存職司之緣故,故此,公文寫作真情流露,只不過謠詠類文體有所不同耳,今人談抒情傳統,除非對“情”內涵作出限定,否則,緣於情的複雜性,這些實用性或公文類文體被忽略了,、歆及劉勰古人觀念。
任筆沈詩,其實有軒輊價值,不容厚此薄彼。
一言以蔽之,似是而非地談論中國文學抒情傳統,有違背歷史事實之虞,應做反思。
《漢書·藝文志》“七略”分類,“六藝略”“春秋”類首列“《春秋經》十二篇”,此即《春秋左氏傳》。
《春秋》二十三家,反映中國源流長史官文化傳統,雖前漢《公羊》、《榖梁》立於學官,但是,作為涓涓細流,後世開出“史學”一部者,非《春秋左氏傳》屬,故《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二十三家後,、歆評曰:“仲尼思存前聖業……故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人道,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定曆數,藉朝聘。
”提升左丘明作為孔子門弟子《春秋》學領域地位。
《春秋左氏傳》《太史公書》降,因而,從《春秋》類四部或四庫經子史集或經史子集“史”,中國積累起無敍事傳統。
但《春秋》大義而言,皮裡陽秋,一字褒貶,善善,懲惡揚善,俱有情感力量,不能以為抒情無涉。
《文心雕龍·宗經》篇談及:“紀傳盟檄,則《春秋》。
”《漢志》,《春秋經》開史傳文體先河,劉勰推流溯源,“《春秋》經傳,舉例發凡”,深諳史傳文體、條例之緣起和演變,故而其《文心雕龍·史傳》篇,於中國敍事傳統總結,見解公允。
延伸閱讀…
紀昀譏諷彥和“史事當行”[22],範文瀾《文心雕龍注》批駁,指出劉知幾《史通》精義“而彥和開其先河”[23];明代王惟儉《史通訓詁敍》雲:“餘既注《文心雕龍》畢,因念黃太史有云:‘論文《文心雕龍》,評史《史通》,二書不可不觀。
’實有益於後學,復取《史通》注之。
”[24]此黃太史北宋黃庭堅,而《文心雕龍》並不可“論文”一端限矣,其《史傳》篇中國史學史上大手筆。
因而,受黃庭堅影響,明清時期,有學者二書兼治者,他們理解二書之間存在著內關聯。
《文心雕龍·史傳》篇雲:“然睿旨幽隱,經文,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創為傳體。
”劉勰明確指出左丘明《春秋左氏傳》於史傳中國史學或者敍述傳統,實具有發軔功。
這是基於《漢書·藝文志》所得出結論。
《文心雕龍·史傳》篇曰:“愛奇,條例踳落失,叔皮論詳矣。
”詹鍈《文心雕龍義證》引郭預衡《文心雕龍評論作家幾個特點》所云:“《史傳》篇沿襲了班彪《史記》批評……沒有正確指出《史記》文學方面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這顯然是受了儒家為正宗思想影響緣故。
”[25]西漢揚雄以來,司馬遷《史記》“實錄”和“愛奇”矛盾,有微詞[26],而作為分體文章學小史,《史傳》篇文體論重點於崇尚“良史直筆”,而探討史傳敍事功能,以及史筆得失,劉勰信奉史傳寫作中“務信棄奇要”[27],此完全符合史傳文體特質,上述郭預衡指責,純屬謬誤,不能令史家為追求所謂“文學方面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而史家求職責,否則,淆亂文體,本末倒置,後人可以《史記》裡讀出“無韻之《離騷》”的況味,然而,史家卻不能以此寫作目標。
兩漢時期,前漢,雖然《春秋公羊傳》學,現實政治中作用,然則史料文獻層面,《春秋左氏傳》價值無可匹敵,徐復觀《中國經學史基礎》認為:“第二點、是《史記·儒林列傳》中言及《毛詩》及《左氏傳》,這是受到五經博士限制……但他《十二諸侯年表序》中,實以《左氏傳》傳春秋意義於《公羊》、《榖梁》;且《十二諸侯年表》及有關《世家》中,採用《左氏傳》,且採《左氏傳》中‘君子曰’。
他《儒林列傳》中言及《左氏傳》,只能推及此乃五經博士中未立《左氏傳》博士故。
”[28]徐氏此番言論闡述了《左氏傳》意義;王充《論衡·案書》篇雲:“《禮記》造於孔子堂,太史公漢之通人,左氏言二書合。
公羊、穀梁寘、胡母氏相合。
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聞不如見。
”[29]司馬遷及、歆父子降,他們推崇《左氏傳》,《春秋左氏傳》奠定中國史學基礎,故而,《春秋左氏傳》史筆,肇始文章敍事學,此劉勰整個文章學體系影響。
《文心雕龍·史傳》篇歷數:“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言經則《尚書》,《春秋》。
唐虞流於典、謨,夏商於誥誓。
洎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紬三班歷,貫四時聯事。
”[30]此祖述《漢書·藝文志》者。
魯春秋記事繫年月日,史學時間空間概念得以確立,此於中國敍事學產生劃時代影響。
《文心雕龍·史傳》篇雲:“蓋文疑闕,貴信史。
”[31]而此種史學意識,擴展開去,以致各體文章遵循不違原則。
《文心雕龍·史傳》篇認為《史記》體例“雖古式,而得事序焉”[32],太史公後世史書敍事樹立了範式,而摸索出此種“得事序焉”範式,司馬遷具有開創功!《文心雕龍·史傳》篇曰:“然紀傳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
歲密,事積起訖疏,斯固總會。
或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失於復重,病於不周,此銓配。
”[33]談史料處理,“按實而書”乃史家要務,緣此,摒絕穿鑿附會杜撰。
所以,《文心雕龍·原道》篇曰:“炎、皞遺事,紀《三墳》;而年世渺邈,聲採靡追。
”[34]遠古事,於文獻徵,後世不能得其彷彿,而傳説則應列於存疑範疇,劉勰此種看法,司馬遷並無二致。
《文心雕龍·徵聖》篇曰:“故《春秋》一字褒貶。
”[35]文字善善,能量,劉勰服膺《春秋》,主要是指《春秋左氏傳》。
《春秋》固屬於劉勰宗之《五經》之一,《春秋》既關乎“言有序”,“言有物”[36],此令他史家眼光來審視文章,此在《文心雕龍》探討各體文章時候,有所呈現,此是劉勰論文之一特點。
劉勰重視各體文章敍事,《文心雕龍·誄碑》篇曰:“孝山、崔瑗,辨絜參,觀其敍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周、胡眾碑,莫非。
其敍事該而要,其綴採雅而澤。
”[37]《文心雕龍·哀弔》篇雲:“及潘岳繼作,鍾其美。
觀其慮贍辭變,情洞悲苦,敍事如傳。
”[38]此三處涉及“敍事”,或如傳,或該而要,道出此類文體悼念逝者,其敍事既要具備傳記功能,但是,可謂傳記而微者,屬於史傳敍事變體。
至於敍事,文辭相配,史實端賴文辭鐫刻於時空維度之內。
《文心雕龍·徵聖》篇曰:“鄭伯入陳,文辭功;宋置折俎,多文舉禮。
此事績貴文之徵。
”[39]《文心雕龍·宗經》篇雲:“故《繫》稱:旨、辭文,言中事隱。
”[40]此觸及敍事中文辭超乎言表功能,可以引發讀者遐思,實與詩歌相通。
而“宗經”所得“體有六義”之一:“三則事信而。
”敍事守法度,則可以避免。
故而,《文心雕龍·正緯》篇所謂:“原夫圖籙見,乃昊天休命,事瑞聖,義非配經。
”[41]若質“事信”、“信史”,緯書之流敍事際上起到“瑞聖”作用,譬如達成“宣漢”目的,所以,其性大打折扣,此,古來士人瞭然於心,所以,它們“義非配經”,“其偽有四”,其性質不可經典等量,只不過“事,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42],觀其敍事徵,譬如想象奇特而,語辭如華滋曄曄,雖無益經典,文章有啟迪,,此溢出對“史傳”文體約束,適合滋潤詩賦文體。
如此經典裁判文章標準,基點於可信,觀《文心雕龍·辨騷》篇雲:”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
”[43]若合乎《左氏》,其敍事不可信;《文心雕龍·辨騷》篇雲:“觀茲四事,於《風》、《雅》者。
”曰:“摘此四事,典者。
”所謂兩個“四事”,涉獵《離騷》敍事,何以《風》、《雅》及經典,劉勰判斷,顯然出於其史家立場。
《文心雕龍·諸子》篇評曰:“管、晏屬篇,事核而言練。
”[44]《文心雕龍·銘箴》篇曰:“其取事核以辨,其摛文簡而,此其。
”[45]《文心雕龍·哀弔》篇稱讚:“賈誼浮湘,《弔屈》,體周而事核,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作。
”[46]《文心雕龍·雜文》篇雲:“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
使義明而詞凈,事圓而音澤,磊磊轉,可稱‘珠’耳。
”[47]《封禪》篇:“及光武勒碑,文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鈎讖,敍離,計武功,述文德,事核理舉,華而實有餘矣!此二家,並岱宗實跡。
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
”[48]《議》篇曰:“郊祀洞於禮,戎事於兵,田穀曉於農,斷訟務於律。
然後標以顯義,正辭,文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明核美,不以深隱為奇:此綱領大要。
若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騁其華,固為事實擯,設得其理,遊辭埋矣。
”[49]上述文體牽涉到敍事準確性問題,屬辭者運用文字技巧結撰文章,但是,事核、事實及事圓要求不可違背,作者舞筆弄文,即使花團錦簇,如果有悖敍事,會導致適得其反結果。
《後漢書·班彪列傳》記載:“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議者鹹稱二子有良史。
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
”[50]關於如何評價作家作品,以及如何規範文體敍事、情致,劉勰相應地崇尚“事核”,主張敍事、,文辭,方能令文積聚起內力量,發揮效用。
《文心雕龍·明詩》篇雲:“造懷指事,不求纖密;”[51]詩歌具有敍事性,抒發懷抱敍述事件須臾不可分離,但是,作為詩歌文體,其敍事帶有跳躍性,顯得簡約,所以不求完備,以求符合詩歌文體特點。
《文心雕龍·諧隱》篇定義:“‘讔’者,隱。
遯辭隱意,譎譬以指事。
”[52]中可以窺見,無論如何故作,後有所指事,脱其敍事性質。
《文心雕龍·論説》篇雲:“‘序’者次事。
”[53]具有安排敍事次第意味,與“言有序”意近,《文心雕龍·章句》篇曰:“事乖其次,飄寓而。
”[54]牽涉古代敍事學課題。
總而言,劉勰秉承《春秋左氏傳》史學精神,一部《文心雕龍》中闡釋了豐富的敍事學觀念,應視其文章學內涵。
至於敍事和作者主體意識即史家立場,或者與抒情關係,其實贅言。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二十三家後,、歆評孔子和左丘明修《春秋》曰:“有所裦諱貶損”,史家每一個字都藴藏著情感,史家激情張力鬆懈,產生不了史學。
如果晉宋之間詩人陶淵明例,可以佐證筆者上述意見。
陶潛“讀書”,典型地呈現其儒道融會思想結構,儒家講有所不為,即使人性喜歡,但是,不以其道得,逾越了道德底線;而莊老道家則開悟人生乃是一過程,人所得,屬餘食贅行,因此,人生所謂,並無任何意義。
因此,高尚之士與此世界聯繫,限度而言,自己和家人衣食、居所所得,如果有酒更佳,而已!《歸去來兮辭》謂:“缾無儲粟,生生資,見其術。
”[55]要解決斷炊問題,一則躋身仕途令陶潛產生屈辱感,《感士遇賦》雲:“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既軒冕之非榮,緼袍恥……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市朝。
”[56]故而返歸田園,唯有腳踏土地,方能令外界一切扭曲自我雜務,於是根斬除,陶潛《勸農》雲:“,抱朴含真。
”[57];二則歸耕,生存以為繼。
而在精神上如何自我慰藉,找到聽內心召喚理由,其《五柳先生傳》雲:“褐穿結,簞瓢屢空。
”[58]“居陋巷”顏淵自比,會激發起精神支撐,於是,羲農、容成氏、老彭、陶朱公、伯夷、王子喬、孔子、顏淵、原憲、楊朱、黔婁、荊軻、揚雄、二疏、袁安、張仲蔚,,這是一個“憂道不憂貧”聖賢譜係,另有《史記》、《漢書》以至近代無數賢人智士,其筆下,沓來。
陶潛《飲酒二十首》之一雲:“少年人事,遊好六經。
”[59]陶淵明深諳《詩經》及《春秋左氏傳》學,對《史記》、《漢書》傾注關注。
因此,陶詩乃抒情和敍事結合典範。
,陶氏涉及詠史詩,譬如《扇上畫贊》所詠八位歷史人物,有事跡載於文獻,陶淵明藉助緬懷這些古人,抒發其“飲河既,休”人生觀念[60]。
其次,陶氏櫽括史料詩,《文心雕龍·熔裁》篇曰:“所司,職熔裁,檃括情理,矯揉文采。
”[61]原文,變換文體,詩形式來演繹歷史事件和人物,此陶詩中,例如《詠二疏》,就出於《漢書·二疏傳》本事;而《詠三》乃《詩經·秦風·黃鳥》以及《左傳·文公六年》記述;至於其《詠荊軻》則一本乎《史記·刺客列傳》。
陶潛既於歷史材料,曲盡其身世遭際,同時表達自己感慨,此輩古人激起了陶氏內心情感之波瀾。
第三,比興新用詩,舉《詩經》之比興,多使用篇首,而陶潛則不然,比興手法其手上,發生創造性變化。
儒道思想浸淫之下,鑄陶潛高尚人格情操,故此,觀其田園詩,涉筆,筆端景物人格化了,突破儒家比德侷限,一切景物描寫和符號性、敍事性存在著不解之緣,引發讀者關於出典遐想。
《南齊書·樂志》雲:“永明六年,赤城山雲霧開朗,見石橋瀑布,所罕睹。
山道士朱僧標聞,上遣主書董仲民案視,以為神瑞。
太樂令鄭義泰案孫興公賦造天台山伎,作莓苔石橋、道士捫翠屏之狀,尋省焉。
”[62]此記載雖晚於陶氏在世年,但是此種表演性藝術形式,當出現。
此可以推測,運筆伎舞,完全可以達成默契無間,陶淵明返歸“舊林”、“故淵”,中,舒展四肢,天人合一,他用身體和心靈去感受,可謂無物不著我情感投射。
我不踐斯境,歲月積。
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
微雨洗高林,清飆矯雲翮。
眷彼品物存,義風隔。
伊餘何為者,勉勵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
園田日夢想,安得離析?終懷歸舟,諒哉宜霜柏。
[63]一反玄言詩、遊仙詩山水詩觀念橫亙心頭寫作窠臼,陶詩回歸感受,於是篇中“微雨洗高林,清飆矯雲翮”,既是騁目見,兼有比興作用,陶氏內心和,便躍然紙上,乃至“素襟”、“歸舟”及“霜柏”,於其內歷史文化積澱,其説是意象,還不如認為具有比興意味,此種漢語“語碼”所包含故事性或敍事性,是不言而喻,這陶潛詩歌將敍事和抒情結合,臻水乳交融範例!而此陶詩中具有普遍性,特例。
關於中國式抒情和敍事點,於受制於其主流學術和文化,以來,儒家居於至尊地位,抒情浪漫性、夢幻性、濃烈度及多樣性諸方面,以及敍事想象力、穿透力、創造力、顛覆性及懷疑精神諸端,均遭儒家思想限制桎梏,故此,程度上構成中國文藝氣質,其間不免存在著負面影響。
若沒有《莊》、《騷》精神補充、刺激,中國文藝遜色。
《漢書·藝文志》有“九流十家”説,明明敍述了諸子十家,何要抹煞其中一家即説家,這令人心生疑惑。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雲:“説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街談巷語,道聽塗説者造。
孔子曰:‘雖小道,有可觀者焉,恐泥,是君子弗為。
’然弗滅。
閭裏知者及,使綴而忘。
如或一言可採,此芻蕘狂夫之議。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方,是九家術蠭出竝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説,取合諸侯。
其言雖,闢水火,相滅相生。
仁之義,敬之和,相反而相成。
《》曰:‘天下同歸而,而百慮。
’今異家者各推所,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合其要歸,《六經》支與流裔。
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折中,股肱之材。
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方今去聖,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
而觀此九家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64]而非要十家裡邊抽去説家這一家,此乃出於深層次考慮。
《史記·老子列傳》所附《莊周列傳》談及《莊子》:“詆訿孔子徒,明《老子》之術。
《畏累》、《亢桑子》屬,皆空語無事實。
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
”[68]《莊子》借無事實之“空語”攻擊儒墨志業,所使用筆墨技巧可謂無所不用其,“街談巷語,道聽塗説者造”?它們《孟子》所謂“齊東野人與”一起,孔子其調侃和嘲諷列,聖賢拉下神壇。
而受眾一端,編造故事,誇大其詞,聳人聽聞,百出,可以滿足芸芸眾生視聽期待,能大行其道,《論語·顏淵》雲:“子曰:‘非禮勿視,非禮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69]現實之相反,於是會形成一股將歷史史實演義化狂潮,令史實淹於戲説之中,歷史事跡因此而盡付笑談中。
這於儒家聖人和《春秋》微言大義構成顛覆歪曲威脅,説家止扭曲了孔子形象,至於令“褒見一字,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70]《春秋》大事失去神聖性和權威性,墮於“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虛無之中。
而歐陽修《崇文總目敍釋》一卷(三十條)“説類”指出:“《書》曰:‘狂夫言,聖人擇焉。
’曰:‘誨於芻蕘’,是説不可廢。
古者懼下情壅於上聞,故每歲孟春,木鐸徇於路,採其風謠而觀之。
至於裏言巷語,足取。
今特列而存之。
”[71]歐陽修則肯定了説家言反映社會現實功能,《漢書·藝文志》恐懼開明包容。
而、歆父子儒家大旗,《漢書·藝文志》裡盛讚儒家“於道”,他們深諳儒家説家不能兼容之事實,因而抑制説家興起和氾濫,其題中應有意。
識中,歷史有不可動搖崇高地位,歷史事實不可篡改,而於歷史是非闡釋,只能服聖人言,如果説家置喙其中,兩者剋,那異端説,驅逐出去。
這規訓了中國敍事性要求,崇尚“實錄”,虛構性敍事則遭到遣蕩,誨淫誨盜禁絕,所以歷史和説不可兩立,唯有犧牲説家才是正道,唯有《春秋經》及其嫡裔才具備敍事合法性。
據上述論證可知敍事和抒情是不可判分,同時,中國式抒情是植根事實基礎上抒情,否則,認為是虛情或濫情。
[1]班固編、顧實講疏:《<漢書·藝文志>講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1。
[2]陳國慶編:《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
[3]章太炎撰,龐俊、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247。
[4]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1。
[5]李零:《上三篇校讀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67。
[6]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頁22。
[7]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15。
[8]於前漢賦地位於歌詩,因此,敍賦談歌詩。
[9]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22。
[10]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601。
[11]陸機著,張集釋:《文賦集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頁99。
[12]陸機著,張集釋:《文賦集釋》,頁20。
[13]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256。
[14]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47。
[15]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240。
[16]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378。
[17]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439。
[18]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65。
[19]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66。
[20]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915。
[21]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136。
[22]紀昀:《紀曉嵐評文心雕龍》(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8),頁143。
[23]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288。
[24]王惟儉:《史通訓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序刻本影印),頁247。
[25]詹鍈:《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579。
[26]見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
頁413、頁507。
[27]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287。
[28]徐復觀:《中國經學史基礎》(台北:學生書局,1982),頁82。
[29]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1163。
[30]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283。
[31]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287。
[32]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284。
[33]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286。
[34]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2。
